网上有关“巴金的《雨》。。”话题很是火热,小编也是针对巴金的《雨》。。寻找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分析,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我多么想再见到童年时期的脚迹!我多么想回到我出生的故乡,摸一下我念念不忘的马房的泥土。”
巨匠上路古井依旧
昨(17)日,文学巨匠巴金逝世,成都是巴金的故乡,在缅怀大师的时刻,请您跟随
本报记者的脚步,去看看那口双眼井……
昨晚,深秋的冷风走遍成都的大街小巷。正通顺街双眼井旁,那株半尺高的胭脂花依然在风中摇曳,虽然没有花朵,但那叶子依然在阴冷的天气中青绿逼眼。
“找到双眼井,就可以找到我童年的足迹”,巴金曾经这样说。人来人往,我走近这口或许是中国文学史上名气最大的一口井———就跟冰心先生那只白色的猫一样,井或者猫,因人崇物。
井已经干枯,上面用两块片石分别盖住井眼,并用石砌栏杆围成四五平方米的一片领地,跟周围的现代化高楼和店铺隔离开来。在井边立有一块石碑,立于1994年,10年过去,碑身的两个小角已经被毁坏,碑身的文字也残缺不全……
站在井边,摩挲着那些质感粗糙的石栏杆,我在想,当巴金还不是一位备受景仰的文学巨匠,而是一个孩童,或是一个少年,那时,他会不会像所有成都孩子一样,曾经在这井边玩过响簧,转过地牛牛?当巴金老人躺在上海的病房里,在他生命的最后一瞬间,他是不是曾经想起遥远成都家乡,想起这口蕴藏他的童年的双眼井? 早报记者罗巨浪
巴金的童年足迹
除了巴金在《我与文学50年》中对“家”的叙述,巴金胞弟李济生日前也证实:“我老家,是在成都正通顺街,又叫双眼井。是我祖父在那里置的产业,我祖父在清朝做过几任县官,后来他就辞官不做了,有几个钱嘛,就在成都买房子。”
记忆·一口老井和一株老树
成都正通顺街的双眼井边,即现在的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所在地,就是巴金度过了19年青年时代的旧居。他的许多主要作品都是以当年的这个老公馆为背景写作的,如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和《憩园》等。很多喜欢巴金的读者包括一
些外国读者,到成都都想造访这个老宅子,但随着城市的变迁,如今能记忆的也只有一口老井和一株老树了。
纪念·青年画家创作成《家》
巴金旧居还引出很多故事:一位青年画家以这棵大树为背景画了一幅叫做《家》的油画,这幅油画曾参加国内外的多次画展,深获好评。巴金把刊登这幅画的画报送给了日本著名作家水上勉先生。水上勉有感于此,还给这位中国青年画家写过信,送过书,演绎了一段中日友好的佳话。这位画家就是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舞美设计师贺德华。
考证·专家精心复元“老家”
战旗歌舞团还有一位老人张耀棠,花了多年的心血考证、制作出一幅宝贵的巴金老家复原图。张耀棠是原战旗文工团团长,他说:“1952年9月我就到成都来了,听人家讲,我们住的这个院子就是巴金的故居,里头有5个井,其中一个井就是小说《秋》里面淑贞跳的那个井。还有一个小荷花池,有人讲,这就是鸣凤自杀的地方,其说不一。我在这个院子里头住了快要30年了,巴金的家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们有责任把它搞清楚啊。”
省文联主席、巴金侄儿李致曾谈到,上世纪80年代曾提出过要恢复巴金故居,巴老不愿花国家的钱为自己做什么,巴老说过:“只要双眼井在,我就能找到童年的路,要纪念的话,写一个牌子就可以了。”
□巴老遗憾
三部曲少了“成都”标签
成都老作家冯水木早前回忆了1967年和巴金的一次谈话。巴金当时谦虚地指出了《家》、《春》、《秋》的不足。回忆起当年的情况,冯水木显得非常激动,“我当时的理想就是当作家,巴金的作品给我影响最大。1967年12月份,我专程去上海探访巴老。当时巴老穿一套蓝色中山服,脚上是一双灯心绒棉鞋,正在上海作协的院子里捡石头,而在他后面的墙上,还贴着一份他写的‘检讨’。”
巴金是怎样观察繁星的,有哪些感受?
曹禺(1910年9月24日—1996年12月13日),原名万家宝,字小石,小名添甲,曹禺笔名的来源是因为本姓“万”(繁体字),繁体万字为草字头下一个禺。于是他将万字上下拆为‘草禺’,又因“草”不像个姓,故取谐音字个‘曹’,两者组合而得曹禺。汉族,祖籍湖北潜江,出生在天津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里。是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成就最高的剧作家。曹禺自小随继母辗转各个戏院听曲观戏,故而从小心中便播下了戏剧的种子。其作品《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的出现也标志着中国现代话剧艺术的成熟,被人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1996年12月13日,因长期疾病,曹禺在北京医院辞世,享年86岁。
作品:五幕剧: 北京人、王昭君、胆剑篇、屈原;四幕剧:?雷雨、日出、蜕变、原野、家、桥、黑字八十二(又名:全民总动员);三幕剧:明朗的天;独幕剧:正在想、镀金;**剧本;艳阳天。戏剧理论:编剧术、曹禺论创作、论戏剧。翻译作品:1946年罗密欧与朱丽叶。散文书信:书信集:曹禺致李致书信(李致 编);散文集:迎春集。
艺术特色:
戏剧结构:矛盾冲突是曹禺戏剧结构的核心,曹禺早期戏剧的结构设置紧紧围绕矛盾冲突展开,冲突多变且因剧而宜。在多变戏剧冲突下,曹禺早期剧作有共同的精神内质的,即对原始野性的讴歌赞美。如《原野》中描绘的原始的美,仇虎在原始森林中奔跑,“大地轻轻地呼吸着,巨树还那么严肃,险恶地伫立当中。”但是,对原始野性的讴歌赞美在曹禺后期剧作中退却消失,戏剧冲突也随之匮乏。 而其剧作的整体结构模式则是由锁闭世界和旁逸而出的新世界构成。曹禺以“家”作为锁闭世界的表达方式,而以“出走”作为走出锁闭世界、寻到新世界的手段。其早期剧作结构模式的发展过程正是新世界逐步战胜锁闭世界的过程,这一过程生动的体现在里《雷雨》到《北京人》的创作过程中,《雷雨》是封闭式的代表作,而后的《日出》、《原野》则开始体现在封闭世界缝隙中寻找新世界,随着锁闭世界的崩溃,新世界成为丰体结构模式。同时曹禺善于化用戏剧情,情节是戏剧结构的重要因素。剧作构思首要来自对生活素材、印象的重新组合,但是,对固有戏剧情节化用、重构和再创造也是剧作构思的一重要来源。曹禺剧作的诸多情节正是来自对中外戏剧情节的化用和重构。戏剧情节的化用是曹禺剧作结构的一大特色。 剧作结构的诗化则是曹禺戏剧的另一大特点。追求诗性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发展方向,曹禺曾说过《北京人》是他当诗来写的,而另一部剧作《雷雨》虽然并非有意为之,依然存在浓厚的诗意,这使得《雷雨》的环境氛围描写显得异常郁闷但是极富深意。在中国传统文化浸染与西方戏剧的借鉴下,曹禺注重诗意与剧作结合,取得了很高成就。曹禺剧作结构的诗化主要体现于语言和戏剧性情境。[13-14] ?
语言风格:曹禺的戏剧语言极具特色,从而使得他在处理戏剧冲突当中,能深入剧中人的内心世界,或则表现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心灵交锋,或则刻画剧中人内心的自我交战。表面的争执、外部的冲突都包蕴着剧中人的内心交战。一切外在的冲突、争辩与日常生活场景,都是为了酝酿、激发与表现内心冲突。语言个性鲜明的性格化是优秀戏剧的一大特色,同时也是曹禺戏剧的一大特点,曹禺笔下的人物个性化语言,非常突出。如《日出》中李石清:“你简直就是个大废物”,这个世界不是替你这样的人预备的。”寥寥数字,充分地暴露了李石清阴险卑劣、残忍无情、无耻的思想性格。《日出》中这样的几乎没有特别拗口的台词,做到了通俗易懂,精练深刻。而且,台词里充满了精妙的停顿和省略,使观众随着剧情的发展完全进入台词所创设的情景中。[1] 戏剧语言的动作性指剧中人物不仅表现出在说话,而且出表现人物自身的心理活动、思想感情,它是和手势、表情、形体动作结合在一起的`,推动着剧情的发展。而曹禺的语言恰巧也有富于感染力的动作性,如《原野》第三幕仇虎在森林中逃跑的幻觉描写,曹禺别开生面地展示了仇虎的内心悲剧冲突,重现了他所遭受的种种不公,他在种种幻觉纠缠下拼命挣扎、苦斗,反抗意志愈益顽强。[16]?另外蕴含着丰富的潜台词也是曹禺惯用的手法,在《雷雨》中,优秀的潜台词比比皆是如:大海打周萍时所说的“你准备好了?”就是指你是准备好跑了呢?还是准备好挨打了呢?曹禺的语言也是抒情、诗意的。曹禺在创作中运用了一些诗的语言技法如比喻、象征、含蓄等的综合运用,使他的戏剧语言具有浓厚的抒情性。在剧本中,曹禺喜欢对他所描绘的人物进行外貌、性格和身世的具体描述,对人物生活的场景作祥细的说明和描绘。这种语言如同叙事诗一般,具有浓厚的抒情性。那象诗一样的语言,具有浓厚的抒情性,意蕴深厚,发人深思,耐人寻味,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曹禺决不是孤立地、静止地撰写人物台词,而是让人物身临其境地讲话,将刻划人物内心活动的台词同舞台效果、布景的描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产生强烈的戏剧效果。《雷雨》便是是当做诗来写的,其中的许多台词准确地展现了人物的性格,抒发了人物的内心情感。繁漪是一个“五四”以后的资产阶级女性,聪明、美丽,有追求自由和爱情的要求;但任性而脆弱,热情而孤独,饱受精神折磨,渴望摆脱自己的处境而又只能屈从这样的处境,正象作者所说,她陷入了“一口残酷的井”。繁漪在第二幕中那段著名的独白,简直就是一首贮满愤懑与渴望:热极了,闷极了,这里真是再也不能住的。我希望我今天变成火山的口、热烈烈地冒一次,什么我都烧个干净,当时我就再掉在冰川里,冻成死灰,一生只热热地烧一次,也就算够了。我过去的是完了,希望大概也是死了的。哼,什么我都预备好了,来吧,恨我的人,来吧,叫我失望的人,叫我忌妒的人,都来吧,我在等候着你们。繁漪在“宇宙残酷的井里”拼死攀援的艰辛与焦灼、压抑与烦闷,“爱起你来像一团火”,“恨起你来也像一团火”的炽烈阴鸷的个性也都熔铸在这诗里。
“我多么想再见到童年时期的脚迹!我多么想回到我出生的故乡,摸一下我念念不忘的马房的泥土。”
巨匠上路古井依旧
昨(17)日,文学巨匠巴金逝世,成都是巴金的故乡,在缅怀大师的时刻,请您跟随
本报记者的脚步,去看看那口双眼井……
昨晚,深秋的冷风走遍成都的大街小巷。正通顺街双眼井旁,那株半尺高的胭脂花依然在风中摇曳,虽然没有花朵,但那叶子依然在阴冷的天气中青绿逼眼。
“找到双眼井,就可以找到我童年的足迹”,巴金曾经这样说。人来人往,我走近这口或许是中国文学史上名气最大的一口井———就跟冰心先生那只白色的猫一样,井或者猫,因人崇物。
井已经干枯,上面用两块片石分别盖住井眼,并用石砌栏杆围成四五平方米的一片领地,跟周围的现代化高楼和店铺隔离开来。在井边立有一块石碑,立于1994年,10年过去,碑身的两个小角已经被毁坏,碑身的文字也残缺不全……
站在井边,摩挲着那些质感粗糙的石栏杆,我在想,当巴金还不是一位备受景仰的文学巨匠,而是一个孩童,或是一个少年,那时,他会不会像所有成都孩子一样,曾经在这井边玩过响簧,转过地牛牛?当巴金老人躺在上海的病房里,在他生命的最后一瞬间,他是不是曾经想起遥远成都家乡,想起这口蕴藏他的童年的双眼井? 早报记者罗巨浪
巴金的童年足迹
除了巴金在《我与文学50年》中对“家”的叙述,巴金胞弟李济生日前也证实:“我老家,是在成都正通顺街,又叫双眼井。是我祖父在那里置的产业,我祖父在清朝做过几任县官,后来他就辞官不做了,有几个钱嘛,就在成都买房子。”
记忆·一口老井和一株老树
成都正通顺街的双眼井边,即现在的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所在地,就是巴金度过了19年青年时代的旧居。他的许多主要作品都是以当年的这个老公馆为背景写作的,如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和《憩园》等。很多喜欢巴金的读者包括一
些外国读者,到成都都想造访这个老宅子,但随着城市的变迁,如今能记忆的也只有一口老井和一株老树了。
纪念·青年画家创作成《家》
巴金旧居还引出很多故事:一位青年画家以这棵大树为背景画了一幅叫做《家》的油画,这幅油画曾参加国内外的多次画展,深获好评。巴金把刊登这幅画的画报送给了日本著名作家水上勉先生。水上勉有感于此,还给这位中国青年画家写过信,送过书,演绎了一段中日友好的佳话。这位画家就是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舞美设计师贺德华。
考证·专家精心复元“老家”
战旗歌舞团还有一位老人张耀棠,花了多年的心血考证、制作出一幅宝贵的巴金老家复原图。张耀棠是原战旗文工团团长,他说:“1952年9月我就到成都来了,听人家讲,我们住的这个院子就是巴金的故居,里头有5个井,其中一个井就是小说《秋》里面淑贞跳的那个井。还有一个小荷花池,有人讲,这就是鸣凤自杀的地方,其说不一。我在这个院子里头住了快要30年了,巴金的家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们有责任把它搞清楚啊。”
省文联主席、巴金侄儿李致曾谈到,上世纪80年代曾提出过要恢复巴金故居,巴老不愿花国家的钱为自己做什么,巴老说过:“只要双眼井在,我就能找到童年的路,要纪念的话,写一个牌子就可以了。”
□巴老遗憾
三部曲少了“成都”标签
成都老作家冯水木早前回忆了1967年和巴金的一次谈话。巴金当时谦虚地指出了《家》、《春》、《秋》的不足。回忆起当年的情况,冯水木显得非常激动,“我当时的理想就是当作家,巴金的作品给我影响最大。1967年12月份,我专程去上海探访巴老。当时巴老穿一套蓝色中山服,脚上是一双灯心绒棉鞋,正在上海作协的院子里捡石头,而在他后面的墙上,还贴着一份他写的‘检讨’。”
知道冯水木是四川人,巴金高兴地和冯水木拉起了家常,他说,“看到了家乡人,我也想起了家乡菜。我最想吃的就是成都的回锅肉和杂酱面。”当冯水木表示自己最喜欢的小说是《家》、《春》、《秋》时,巴金却说道,“说句老实话,我觉得《家》、《春》、《秋》有个最大的遗憾,没有在书中把成都的街道、桥梁、河流点出来。好多人读了我的书后,根本不知道我写的就是成都,就连曹禺在话剧版《家》的剧本中也是写的西南某城。”
□巴老情结
最爱吃成都的油菜头
巴老在成都有很多老友,著名文人车辐便是其中之一。早前,90高龄的车辐回忆起当年与巴老在一起的日子时,说到他和巴老在一起不聊文学,“摆成都还摆不完,没得时间聊其他的了。”
车老和巴老结缘于上世纪30年代的杂志《四川风景》,随后便成了好朋友。车老幽默地回忆说,他自己是“好吃鬼”,又是一个坐不住的人,喜欢到处寻找好吃的东西,成都的老馆子几乎他都知道。巴老每次回成都都不会“放过他”,要求他当向导寻美食。他指着1993年到巴老家最后一次见到巴老的照片对记者说,每次到上海看望巴老,都会带上30余斤成都才有的蔬菜,青菜头、油菜头都是巴老相当喜爱的蔬菜。
□缅怀巴老
一些手迹
记者在成都图书馆地方文献部见到了由巴金亲笔签名的10本图书,这是1988年“五一”节李致从上海带回的珍贵礼物,而今成了馆藏珍品。据地方文献部主任刘先生介绍,成都图书馆还珍藏有巴老的两篇手稿,刘先生说:“两篇手稿一篇是一本书的《跋》,一篇是读后感想,都是我们文献部很珍贵的资料。”记者看到,巴金亲笔签名的10本图书中有中文版小说《寒夜》、随笔《探索集》、《随想录》、《无题集》、《病中集》、《真话集》和4本俄文、法文版小说《寒夜》等。刘先生说,“1988年李致到上海看望巴老,我们馆里请李致带了几本巴金的书到上海请他签名,结果巴老另外还送了我们10本图书。”
据了解,这几本书,作为珍藏品,不外借。
一尊铜像
为了纪念文坛巨匠巴金百年寿诞,由四川雕塑家严永明设计的巴金铜像2003年6月初在成都制作完成。这尊全国最大的巴老铜像于6月20日安放在成都百花潭公园内的慧园广场。
巴老铜像身着中山装,戴着一副眼镜,围着围巾,手拄一支竹制拐杖,正漫步走向前方。雕塑家严永明介绍说,铜像高2.1米,是用1吨多上好的青铜铸造的,为国内最大的巴金铜像。严永明称,巴金是一个关心民间疾苦的文学家,铜像整体上表现的是巴老的精神境界。
一座纪念馆
巴金文学院新馆于去年在龙泉驿北干道竣工。巴金文学院副院长傅恒透露, “龙泉当地政府为新馆很花了些工夫,新馆的布局采用了对称的四合院结构,中间的一幢建筑最为高大,共分两层,巴金铜像摆放在一楼大厅正中,所有资料和实物展品陈列在二楼。”新馆的主要建筑物有巴金纪念馆、综合楼、会展楼和亭廊,以灰瓦白墙为主,格子窗、坡屋顶,平实的民居风格与巴老朴实的为人和为文相应。各建筑之间分布着高低错落的园林,栽种了成都特有的代表性植物:竹和芙蓉,园内有亭台、小桥、流水等建筑小品。
关于“巴金的《雨》。。”这个话题的介绍,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分享完了,如果对你有所帮助请保持对本站的关注!
本文来自作者[dazhoutv]投稿,不代表大洲号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dazhoutv.com/jingyan/202508-8197.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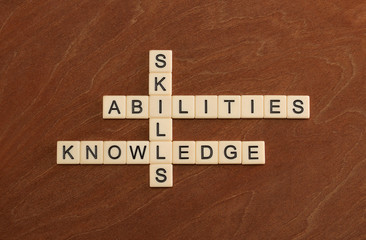




评论列表(3条)
我是大洲号的签约作者“dazhoutv”
本文概览:网上有关“巴金的《雨》。。”话题很是火热,小编也是针对巴金的《雨》。。寻找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分析,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到您。我多么想再见到童年...
文章不错《巴金的《雨》。。》内容很有帮助